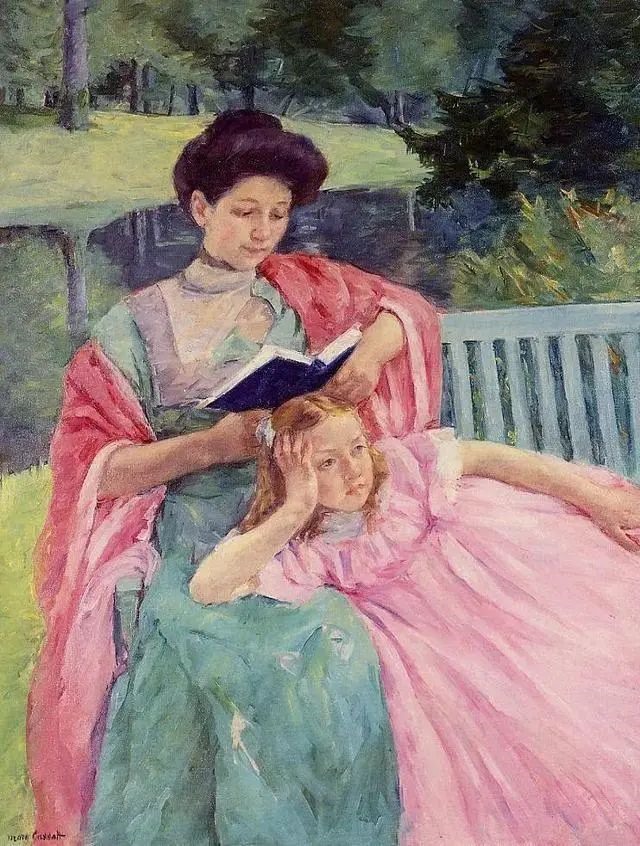
40多年前,我从前门搬到洋桥,那里明显属于城乡接合部的郊区。这完全是我的主意。我去北大荒插队后,街道积极分子中的一位抢占了我家老屋,把我父母挤进了逼仄的小屋。父亲病故后,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,住进小屋,忍受不了窗前全院用的水龙头整天水声哗哗不断。正好洋桥有一位复员转业的铁道兵,他想让孩子到城里上个好学校,看中了我家边上的第三中心小学,便和我各取所需换了房子。
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的选择,离开了我的伤心之地,应该也是母亲的伤心之地。便在暑假母亲去姐姐家小住的时候,麻利儿地搬了家,以为会给母亲一个惊喜。殊不知母亲并不情愿,只是没有表达。前门住了几十年的老街、老院、老屋,纵使有占领老屋的小人,毕竟还有好多善良的老街坊。一种故土难离的感情,在母亲心头升起。
搬到洋桥的第二年,赶上唐山地震。母亲惊醒,喊起我来。幸好小屋无恙,只是屋檐下的蜂窝煤被震倒一片。震后,洋桥这一片地铁宿舍的人全都住进空场上搭建的简陋地震棚。
地震之后没几天,我的一位小学同学,阔别多年之后,向前门街坊问清我洋桥新址后找到这里。她是我童年的好友,“文革”时去了东北,后在哈尔滨读了大学物理专业,毕业后在哈尔滨工作,这一年到上海出差,途经北京。赶巧那天晚上,我们那一排房子突然停电,很多人都从屋里出来。同学自告奋勇地对我说:“有梯子吗?我上去看看。”我找来梯子,跟在她身后爬到房顶。电线就晃晃悠悠地横在上面,不知她怎么三鼓捣两鼓捣,电路接通了,电灯亮了,房下面一片叫好声。
老友走后,母亲对我叹口气说,要是还住老院,用得着人家这样好找?还让人家登高上房给你修电线?我没有想到,除了念旧,还有孤独,已经如蛇一样悄悄爬上母亲的心头,吞噬着母亲的心。毕竟,这里没有一个母亲认识的人,特别是白天大家上班后,更显得寂寥。
一天夜里,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,吓了我一跳。她悄悄对我耳语,生怕别人听见:“有人要害你!你可要注意,要是把你害了,我可怎么办?”我以为她可能是做了噩梦,只是安慰她:“没有人要害我,干吗要害我?您放心吧!”
一直到1977年初的一天,我正带着学生在一所工厂学工劳动,学校的一位领导急匆匆地找到我,对我说,你家里有点儿事,让你赶快回家!回到家一看,屋子里围着好多人,还有一位警察。才知道,那天母亲从家里出走,走到北边不远的凉水河前,想投河自尽。她觉得我已经被害,自己无法再活了。母亲半个身子浸在河水里,被人救了上来。
母亲的棉裤已经湿透,好心的街坊帮母亲脱下棉裤,看着母亲枯瘦的光腿伸进被子里,我的心一阵绞痛,才意识到母亲病了,病得不轻了。
我带母亲到安定医院,医生告诉我,母亲患的是幻听式精神分裂。那一刻,我很后悔这次搬家。我只想到自己,没有设身处地地想想年老孤独的母亲。
洋桥,虽然住了不到八年的时光,对于我意义却非同寻常。它让我认识到了习惯性的世界的结束,也认识到了非习惯性的世界的开始。对于我,习惯性的世界,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,习以为常;非习惯性的世界,则是他人的世界,或者说是客观的世界。从自我的世界跳出来认识真正客观的世界,尽管有些残酷,却是我告别青春期的重要节点。
一年多之后,1978年,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。我报到之后,找到被分配的宿舍,那一晚,怎么也睡不着,我跳下床,骑上自行车,往洋桥赶。我赶到家时,却推不开门,呼喊着母亲,母亲打开门,我才看见门后顶着粗粗的一根木棒。我的心悬到嗓子眼儿,眼泪一下子滚落出来。
我和母亲商量,先送她到姐姐家住,母亲同意了。四年的时光,母亲以她的牺牲帮助我大学毕业,更帮助我认识了从未认识的非习惯性的世界,也认识了母亲的世界。





